2021年,世界依然在疫情的阴影下前行,人们戴着口罩,保持社交距离,生活节奏被彻底打乱,这一年,写实的作文不再只是记录日常琐事,而是成为一面镜子,映照出时代的面貌和个体的挣扎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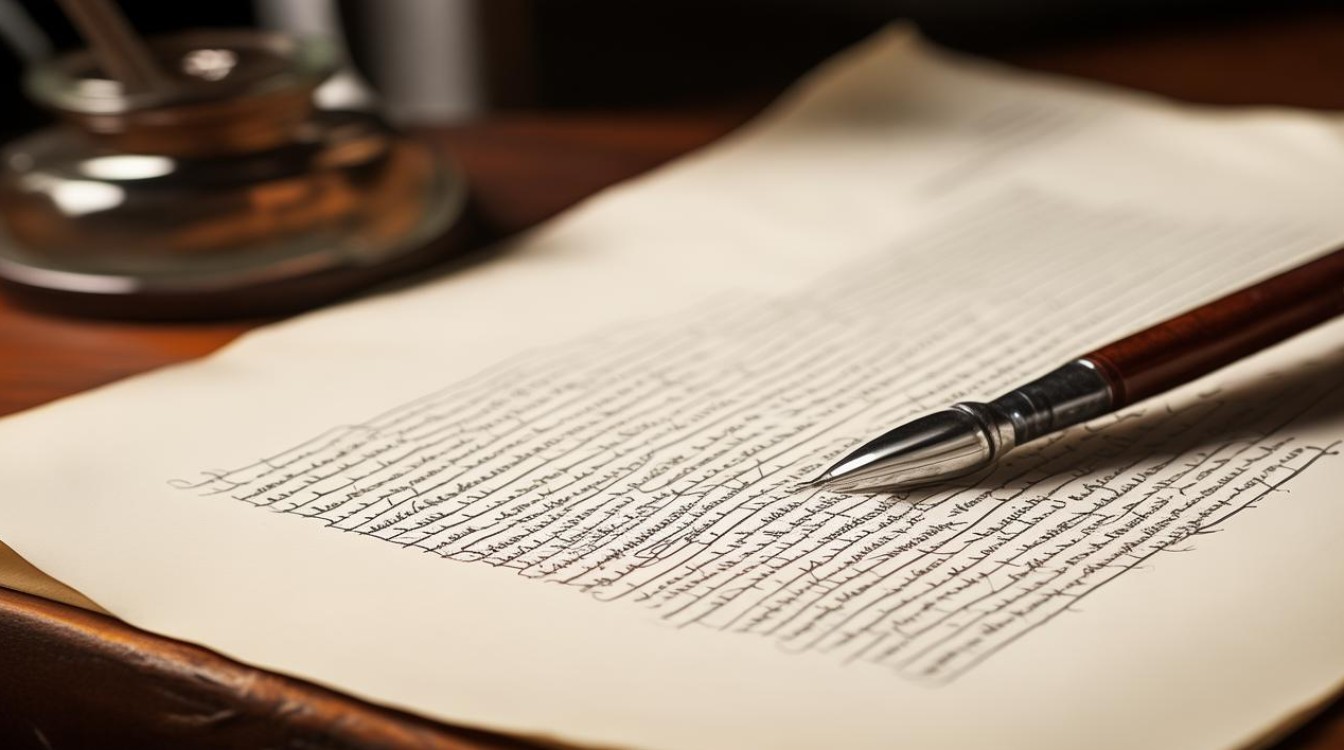
年初的寒风中,医院走廊挤满了等待核酸检测的人,一位中年妇女蜷缩在塑料椅上,手里攥着皱巴巴的挂号单,她不时抬头望向叫号屏幕,眼神里交织着焦虑与疲惫,这样的场景在作文里频繁出现,学生们用稚嫩的笔触描绘着成人世界的重压,十五岁的李婷在作文中写道:"消毒水的气味钻进鼻孔,像一根细针不断刺痛神经,穿防护服的医生走过来时,我能看见他护目镜上的水珠,却看不清他的表情。"
教室里少了往日的喧闹,课桌被拉开距离,同桌之间隔着透明的塑料挡板,语文老师王建国发现,学生们的作文风格发生了微妙变化,过去华丽的修辞少了,取而代之的是具体到分钟的时间记录:"7:20校门口测温,7:35用酒精湿巾擦桌面,9:15班长开窗通风..."这些看似枯燥的细节,拼凑出特殊时期的生存图景,有位学生在作文里详细描写了如何用橡皮筋固定口罩耳带,防止长时间佩戴造成耳朵疼痛,这种具象化的文字反而具有打动人心的力量。
网络课堂成为新常态,初二学生张明的作文里出现这样的段落:"电脑屏幕右下角的小窗口里,能看到同学们模糊的侧脸,有时突然传来婴儿啼哭或锅铲碰撞声,但没人会笑,数学老师的头像卡成马赛克,他的声音像从很远的地方传来:'能听到吗?听到的扣1。'"这种碎片化的叙述方式,恰如其分地呈现了虚拟课堂的疏离感。
菜市场里,摊主老周的故事被多个学生不约而同地写进作文,他的鱼摊总摆着个小黑板,上面用粉笔写着"今日已消毒"和当天的鱼价,有学生注意到他皲裂的手指总贴着创可贴,消毒液让伤口迟迟不能愈合;另一个学生则记录下他教顾客用手机扫码付款时的耐心,这些平实的观察,让普通人的坚韧在作文中有了具体的形状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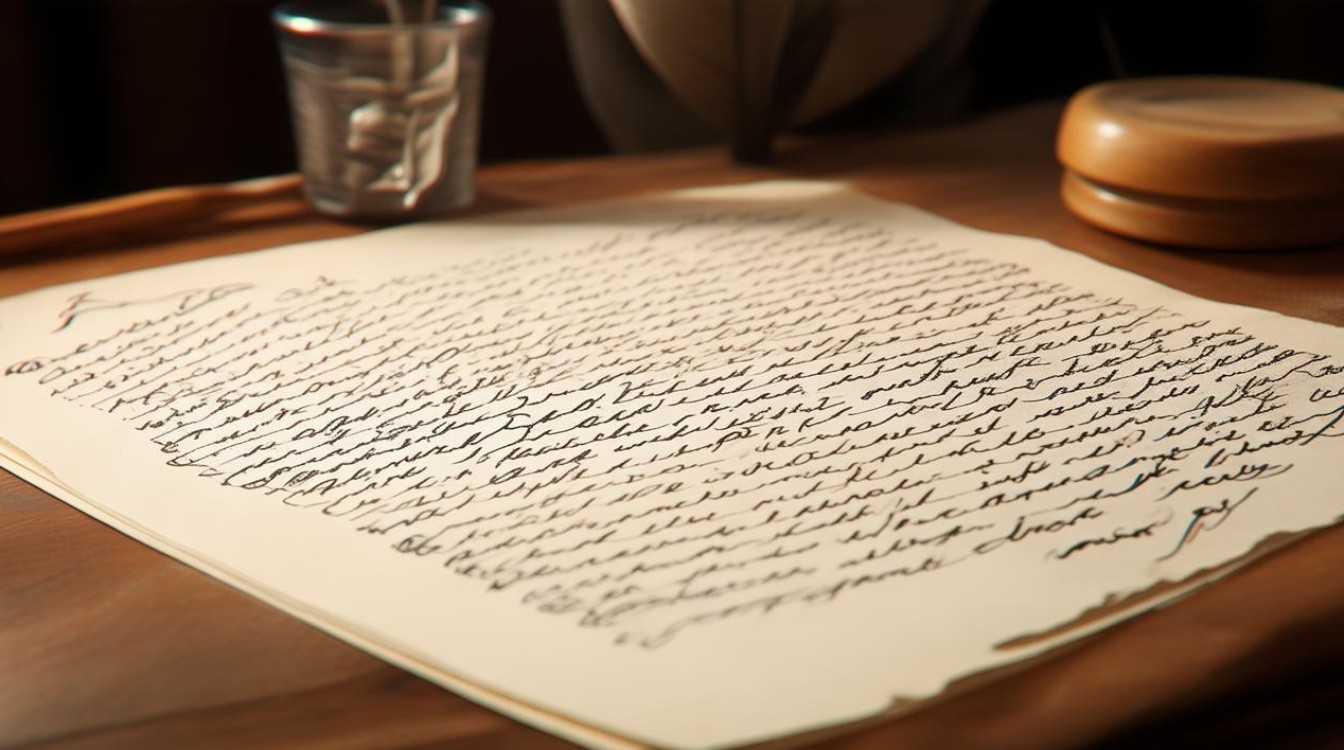
高考延期的消息传来时,高三教室爆发短暂骚动又很快平息,林小雨在当天的随笔里写道:"倒计时牌上的数字突然增加了30天,有人撕掉了刚写完的模拟卷,班主任说这是多出来的复习时间,但我知道,这是30个需要重新熬过的黎明。"这种克制的笔调下,藏着整整一代人的心理褶皱。
夏日的疫苗接种点,成为新的写作素材,有学生细致描写了留观区的情景:老人攥着接种证明反复查看,年轻人低头刷手机掩饰紧张,穿红马甲的志愿者来回走动,塑料椅在挪动时发出刺耳的摩擦声,这些场景通过学生的眼睛观察,再经由文字精确还原,构成特殊年份的集体记忆。
台风"烟花"来袭的那个夜晚,许多作文记录了城市另一面的脆弱,停电的居民楼里,烛光映照出邻居们分享储备食物的剪影;积水漫过膝盖时,陌生人互相搀扶的体温;便利店店员坚持营业到最后一刻,收银台旁堆着沙袋,这些文字剥去了宏大叙事的外衣,展现危机中的人性微光。
秋天的校园运动会上,看台座位保持着安全距离,学生王磊在作文里捕捉到一个细节:跳远比赛时,裁判戴着口罩吹哨,白雾瞬间模糊了哨子,这个转瞬即逝的画面,成为疫情时代体育精神的独特注脚,另一位同学则写了田径场边新设的临时隔离帐篷,"它空荡荡地立在那里,像句随时准备插入的括号"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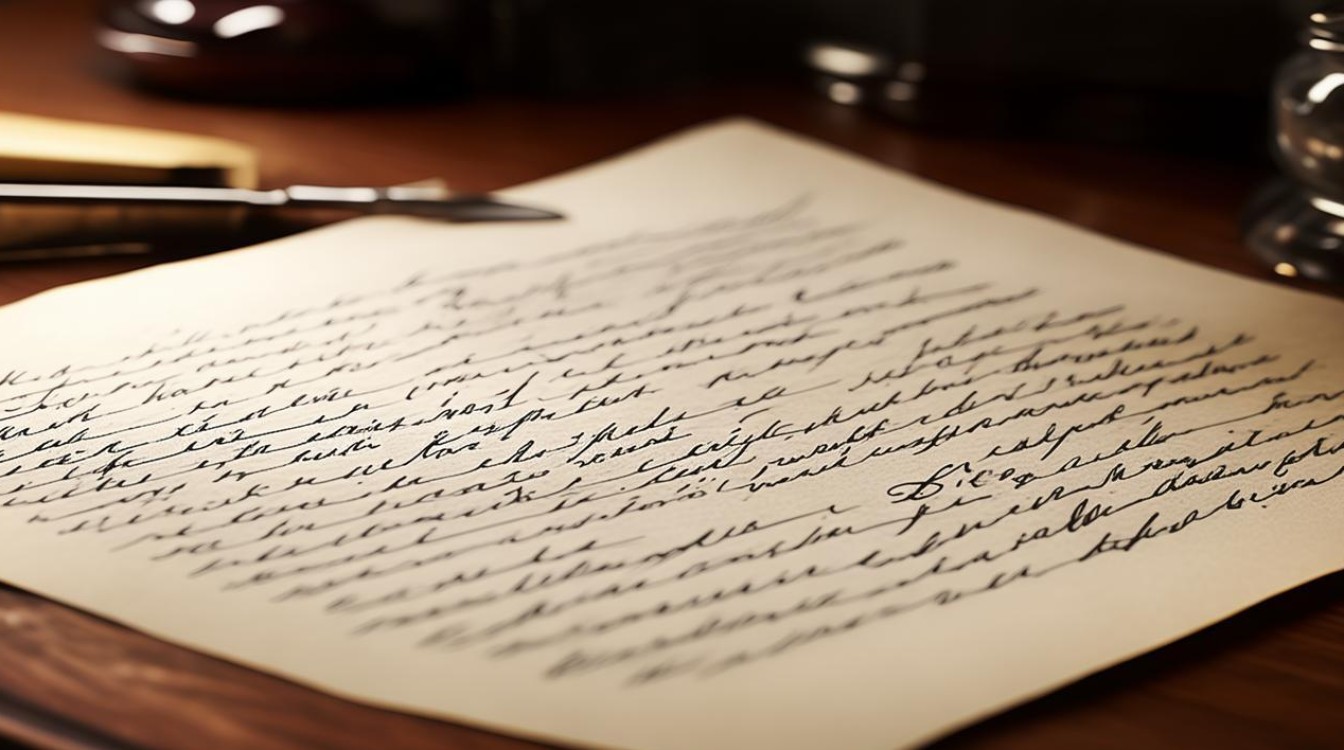
随着"双减"政策落地,教培机构玻璃门上的海报陆续撕下,有篇作文描述了这样的场景:穿着格子衬衫的辅导老师站在空荡荡的教室门口,手里抱着一摞未发完的讲义,阳光透过玻璃照在"限时优惠"的残破字迹上,形成奇特的明暗分割,作者没有直接评论政策,而是用空间意象传递出行业转型的阵痛。
冬至那天,隔离酒店里的留学生陈晨在作文中写道:"窗台上的外卖饺子已经凉了,我蘸着醋看窗外飘雪,手机视频里,家里的年夜饭冒着热气,妈妈把摄像头转向每道菜停留三秒。"这种时空错位的亲情书写,比任何抒情都更令人心酸。
2021年的写实作文呈现出鲜明的时代印记,学生们不再追求辞藻堆砌,而是学会用细节构建真实,消毒水气味的数据线、口罩压痕的深浅、健康码颜色的变化,这些元素在作文中反复出现,形成特殊的审美符号,教师们也发现,当文字回归观察本身,反而能触及更普遍的情感共鸣。
在评阅年终作文时,王建国老师注意到一个转变:往年常见的"难忘的一天"这类题目,现在学生更倾向于写"普通的星期三",有篇佳作这样开头:"清晨六点十八分的闹铃,厨房飘来葱花炒蛋的焦香,妈妈在客厅清点要带的病历本——这是妈妈确诊后的第七个星期三。"这种去戏剧化的表达,反而呈现出生活的本质重量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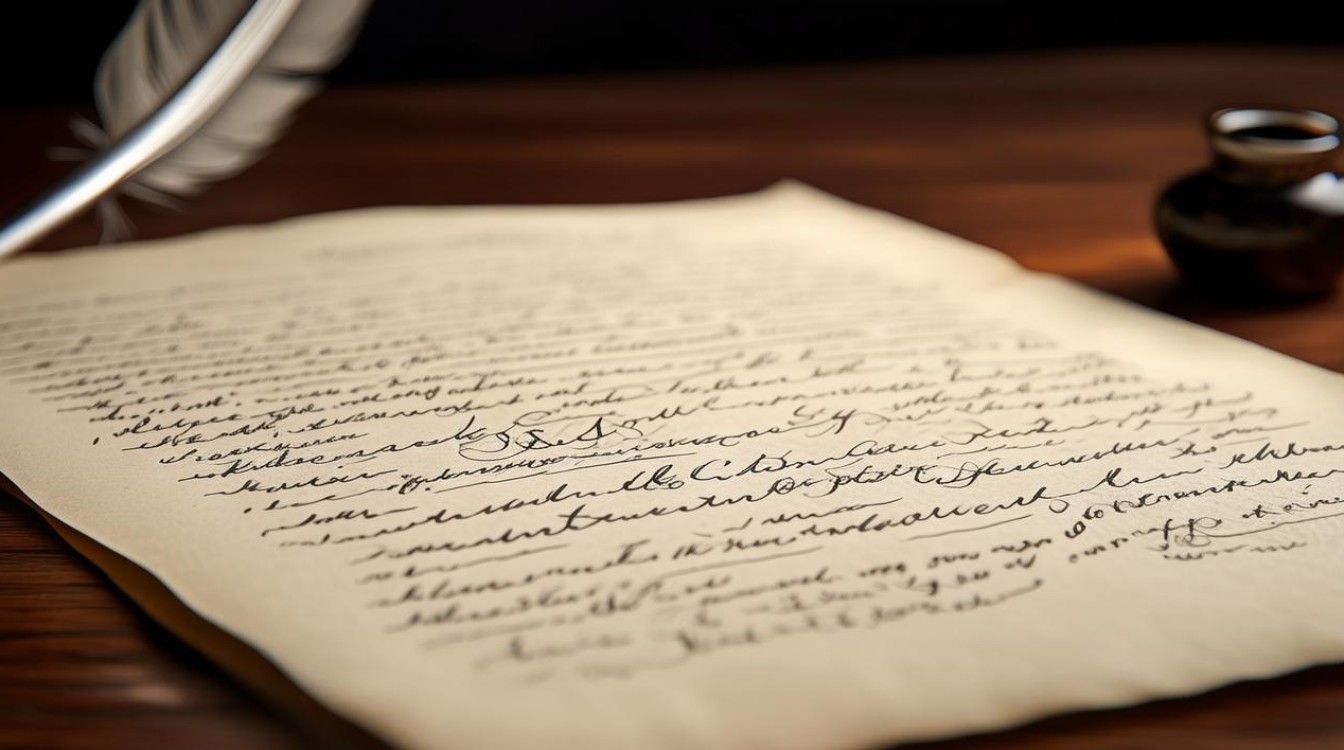
疫情第三年的春节前夕,作文本上出现许多关于"不确定"的描写,有学生写父亲犹豫是否回乡过年时反复折叠又展开的车票;另一个学生记录药店店员说"连花清瘟又断货了"时嘴角的下垂弧度,这些文字像精准的切片,展现社会情绪的真实质地。
当写作回归观察的本源,作文不再只是作业,而成为一代人的生存档案,那些被口罩遮住的表情,被隔离阻断的拥抱,被消毒液浸泡的双手,通过学生的笔尖获得永恒定格,在这个信息爆炸却经验趋同的时代,或许正是这种具体而微的写实,最能抵御记忆的流失。

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