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一次遇见他,是在大学英语角的角落,他戴着一副黑框眼镜,手里捧着一本翻旧的《牛津高阶词典》,指尖轻轻划过纸页,嘴里低声念着单词,阳光从窗外斜斜地照进来,落在他微微蹙起的眉头上,像是给那些陌生的字母镀了一层金边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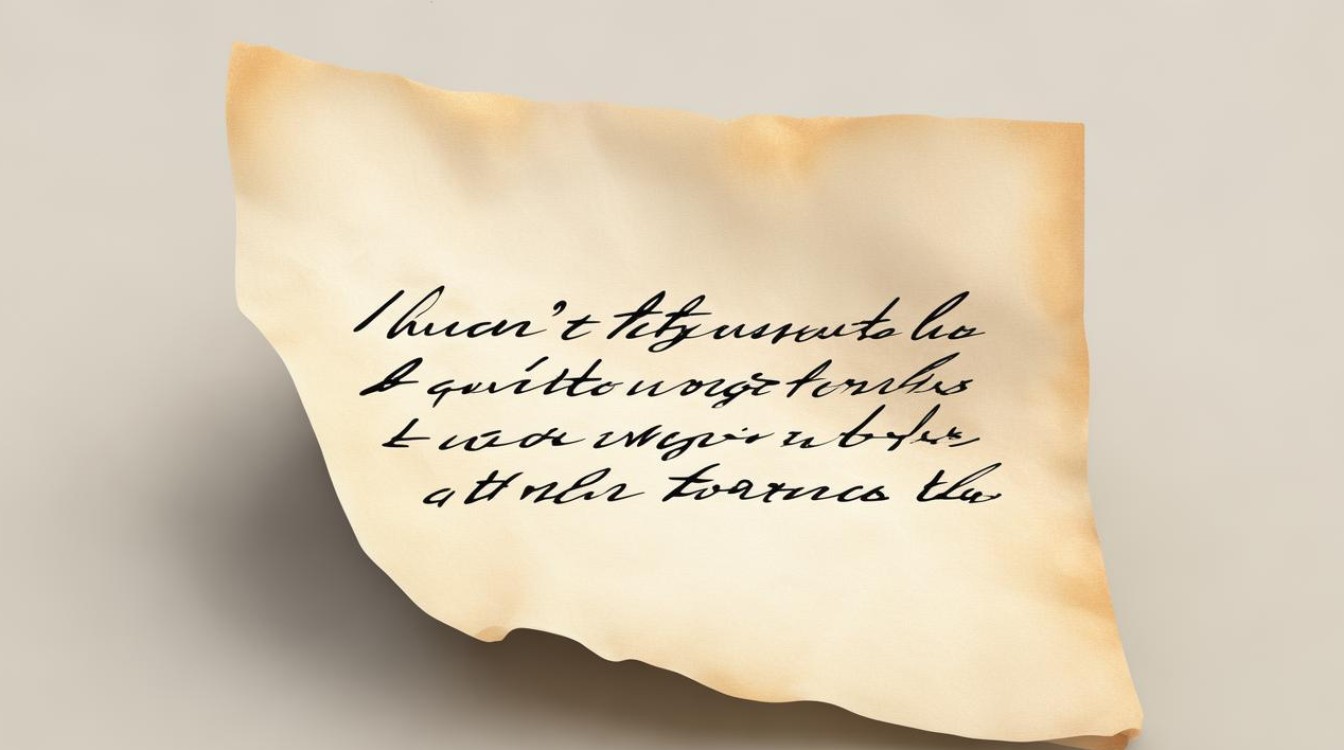
那时候,我的英语很差,每次开口都要在脑子里把中文翻译成英文,再小心翼翼地吐出来,可他的单词量似乎无穷无尽,随口就能说出“serendipity”“ephemeral”这样的词,甚至能用“quintessential”形容一杯咖啡,我问他怎么记住这么多单词,他笑了笑,说:“单词不是背的,是活的。”
他的方法很奇怪,他不抄写,也不死记硬背,而是把单词揉进生活里,比如学到“melancholy”,他会指着阴雨天说:“看,这就是melancholy。”学到“effervescent”,他会摇一摇刚开的汽水,“听到没?effervescent的声音。”单词不再是纸上的符号,而是带着温度的画面、声音,甚至气味。
有一次,我们路过一家面包店,他突然停下脚步,指着橱窗里的牛角包说:“croissant。”我跟着念了一遍,他摇头,“不对,要想象黄油在烤箱里融化的声音。”后来每次看到牛角包,我的舌尖都会自动浮现那个单词,仿佛能尝到酥皮的香气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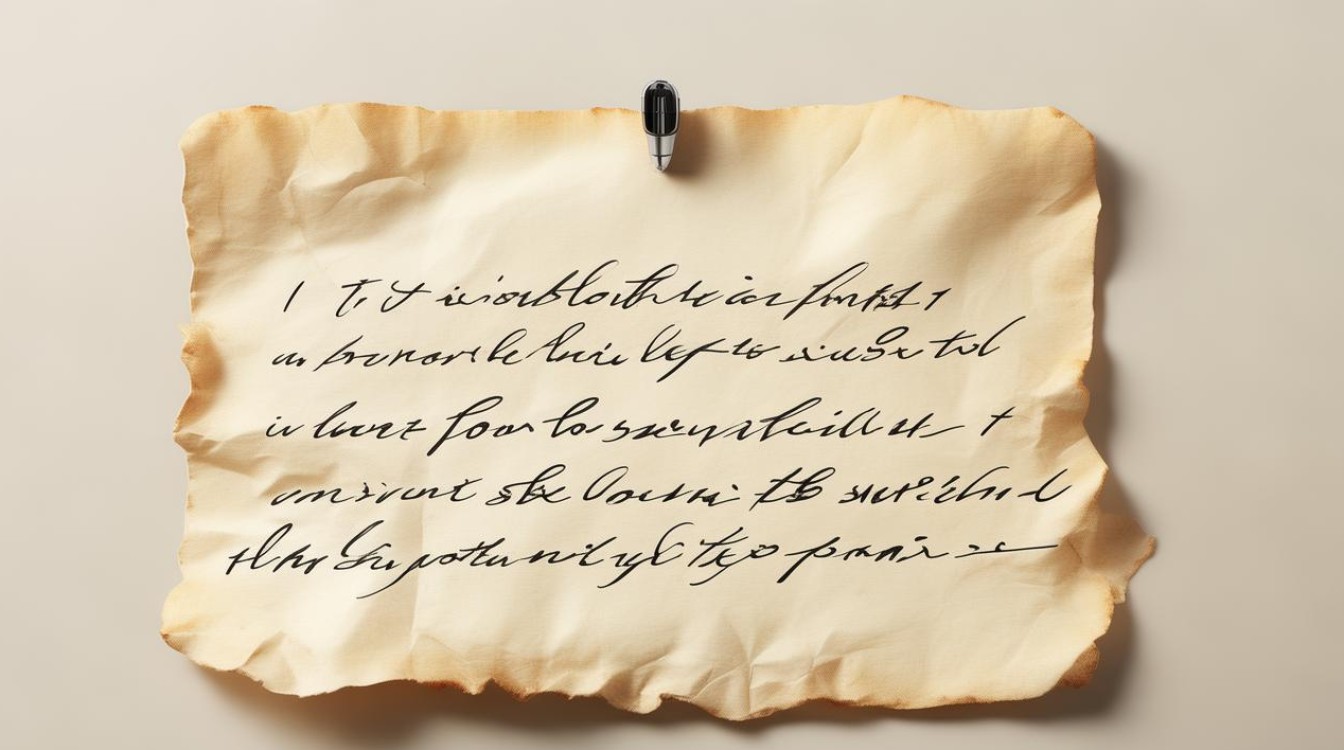
他总说,记单词要动用所有感官,学“petrichor”(雨后泥土的气息),他就拉着我在雨停后的操场散步,深深吸气;学“luminous”(发光的),他指着路灯下的水洼,说那是“luminous puddles”,渐渐地,我的笔记本不再是一串串字母,而是画满小图:一片羽毛旁边写着“plume”,一团火焰旁边标着“scintillate”。
最让我惊讶的是他对词根的痴迷,他说,英语单词像乐高,拆开就能看见故事。“Astronaut”是“star sailor”,“philosophy”是“love of wisdom”,有次我抱怨“pneumonoultramicroscopicsilicovolcanoconiosis”(火山矽肺病)太长,他眼睛一亮:“你看,pneumo-是肺,volcano是火山,连起来就是‘火山灰伤肺的病’。”我突然觉得,这个长得离谱的单词,竟变得可爱起来。
后来他去了国外,临走前送我一盒卡片,正面是单词,背面是他画的涂鸦:一只猫蜷在“nonchalant”旁边,流星划过“serendipity”上空,他说:“别把单词关在书里,让它们跟着你走路、吃饭、做梦。”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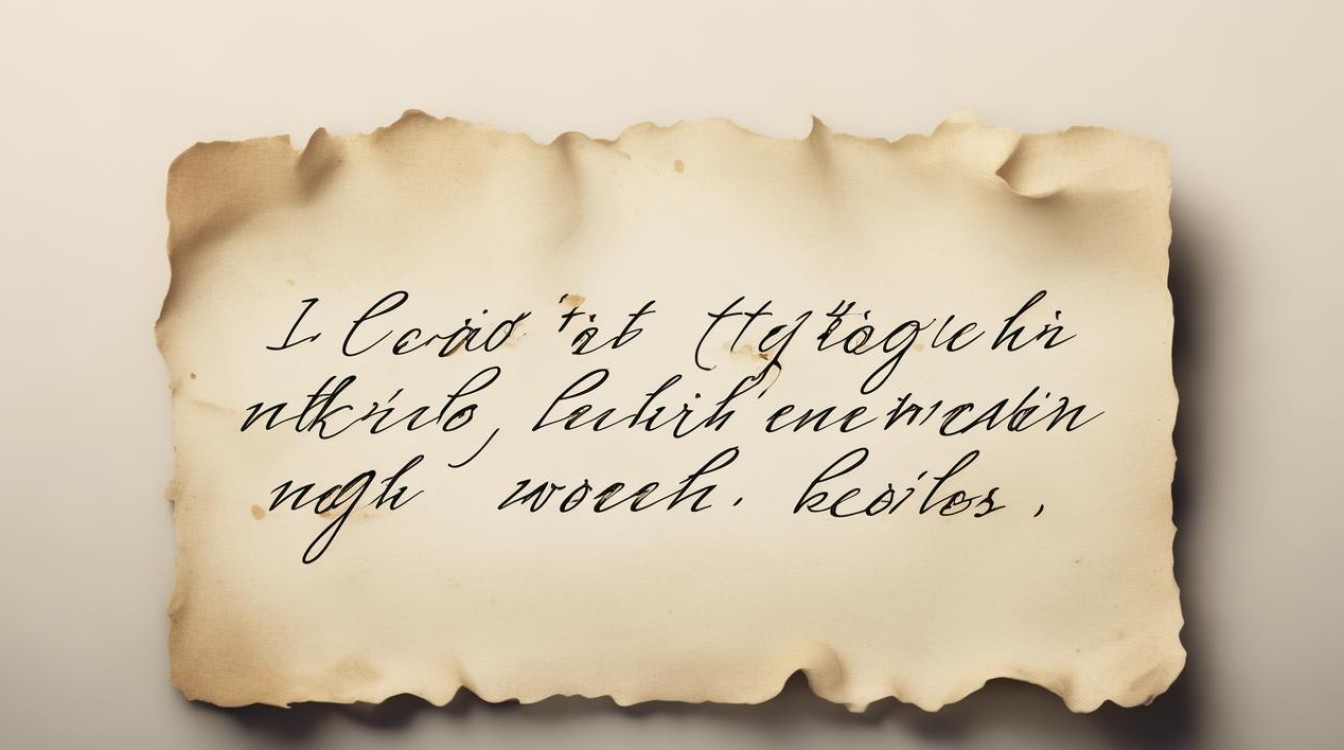
每当听到“rustle”这个词,我依然会想起他踩过落叶的脚步声;看到“gossamer”,眼前就浮现他指着蛛网说“比纱还轻的”,有些人的存在,就像被施了魔法的单词,一旦真正读懂,就再也忘不掉。
如今我的英语早已流利,可每当有人问我怎么记单词,我总会说起那个把“ephemeral”变成樱花飘落的人,或许最好的记忆法,从来不是技巧,而是某个让单词活过来的人。

